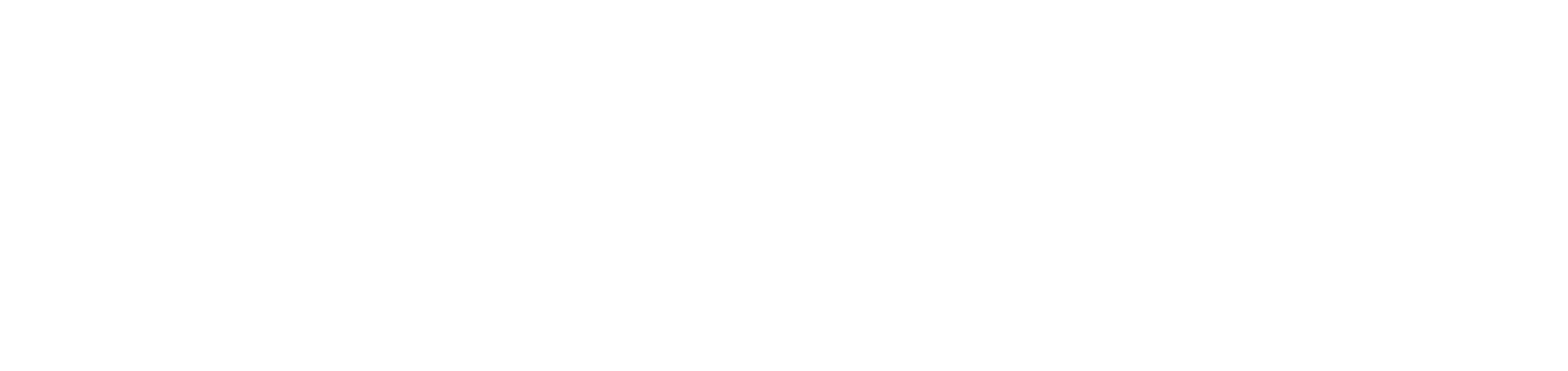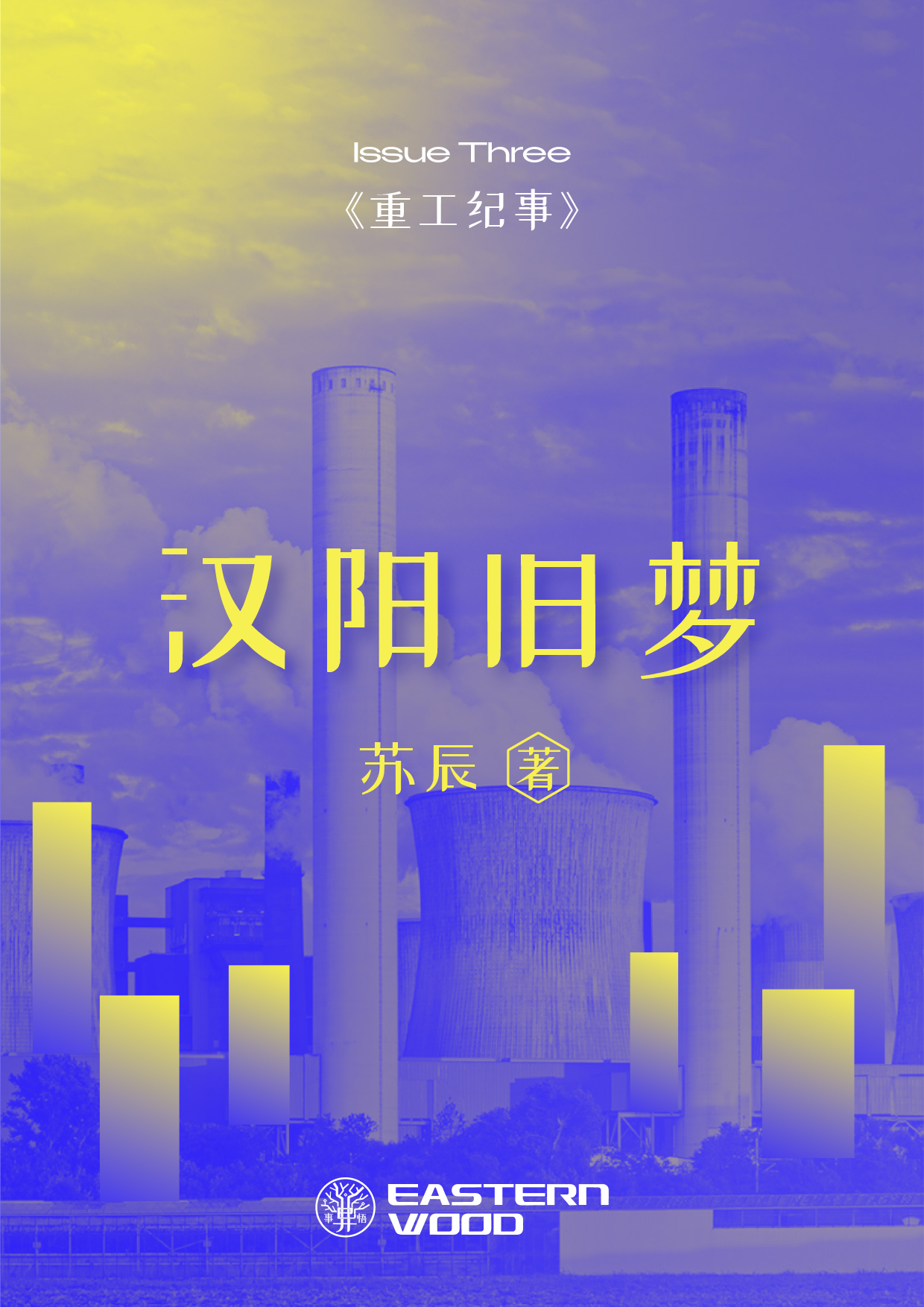全文约12800字,预计阅读时间26分钟
正文:
第一章
我刚毕业那年,远离家乡,在重庆钢厂做技术员。
从办公楼通往车间的路上,有座红砖结构的旧厂房。大门从没开过,三四层楼高的顶棚上长出狗尾草,有麻雀飞进去做巢。
“那是钢迁会的库房,过两年都要拆了,搬到长寿县去。”我师父说。
“钢迁会?”这个名字太过古老,让我意外。
“对,日军入侵的时候,民国政府成立钢迁会,把汉阳铁厂的设备运到这。”师父说着,指了指顶棚上野草摇曳的红砖缺口。
“那就是日军空投炸弹的弹坑。当年组装时常有空袭,被炸伤的废件就存在那,一直没处理过。”
钢迁会是重庆钢厂的前身,1938年成立,1939年在大渡口投产,供应国内军用钢材。而现在,钢铁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。因为产业升级和环保问题,这些都要搬到长寿去了。过了不久,那座红砖仓库也要进行设备盘点。
“判断有价值的东西,或许以后可以放进博物馆。”师父说。
库房里有一股霉味,窄长的阳光从天窗落下来,映出堆叠的废件。这些都是人无法搬动的,只能先盘点外围,再叫叉车。
我穿着劳保鞋踩进去,依次辨别、编号、记录名称。容易辨认的是一些早期转炉配件,实在辨认不出的就按废铁标注。
铁矿石经过高炉冶炼成生铁,再进入平炉、转炉或电炉冶炼成钢。民国时期,贝麦塞转炉炼钢法很常用,所以转炉配件最多。
我将标签写好贴上,正要继续向前,却被什么绊住,撞在劳保鞋前端的铁板上。那是一只铁箱,油漆剥落,棱角锋利。它前面的铁锁已经锈蚀,用力一敲就断成两片。
我蹲下去,打开箱子。里面并排放着一只皮革封面的笔记本,一块长方体试块。
它们太新了,尤其是那试块,看光泽并非不锈钢,表面却毫无锈迹,与旁边锈蚀的铁皮对比鲜明。承托这些东西的是一张镂空铁板,从孔洞里看下去,箱子的下层填满生石灰,大概用来防潮。
我拿起试块,它非常沉,一个角上打着几个字母钢印:HYLn-103。
第二章
第二章
民国九年,秋。
汉口火车站的欧式风格建筑,在一众低矮参差的民房中格外显眼。空气潮热,有一股煤灰和油烟混杂的味道。行人匆匆,对面的房檐下间或有些杂货、洋布店和饭馆的广告牌。
几辆黄包车停在路边,陈文修提着皮箱走出站。阴影里有个青年忽然起身,面露惊喜。
“陈先生!”他喊,同时低头看了看手表,确认时刻。
“北洋大学,机器学本科,对不对?”
“是我。”陈文修转过身,那人和他年龄相仿,稚气未脱。
“何永年,山西大学,采矿冶金专业。师父让我接你。”他跑过来,接过皮箱,朝车夫挥
了挥手。
汉阳铁厂距离车站不远,与大冶铁矿、萍乡煤矿同属于汉冶萍股份有限公司。这里临近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口。虽已入秋,黄包车经过桥面时,仍能看到许多人赤裸上身,一个猛子扎入江中,随波起伏。
陈文修望过去,不觉松开袖口的一颗纽扣,有些心痒。
“文修兄,你会水吗?”何永年似乎看穿他的心思,侧身过来。
“会,小时候我家旁边有条河,我经常去抓鱼。如果允许,这天气去江里最好。”
“当然可以,你得教我。你看,当地人说河底有个藏金洞,水质清的时候潜下去能看到,但还没人游到过呢。”
何永年指着众人扎猛子的方向,有些兴奋。说话间,车夫已慢下来,停在铁厂大门。
在这条路的尽头,一条厂内铁路横贯西东。一头是高耸烟囱的高炉,一头连接贝麦塞转炉车间。蒸汽火车载着装满铁水的鱼雷罐缓慢驶过,留下燥热和烟尘。
“本来我的专业该去大冶矿,但我认为冶铁更需要人才,才申请来这。你呢,文修兄?”
何永年走在前面,将行李交给门卫,嘱托送到宿舍。
“冶铁机器属于机器学的分支,我们课上也讲贝麦塞炉结构。若不能国产钢铁,机器设计总归受制于人。进口一旦被制裁,岂不是要做无米之炊了。所以我想,中国建设工业,必当从产出钢铁做起。”
陈文修说着跟上去。一些工人穿着夹棉的防火服,守在出铁口。面对上千度的铁水,越热倒要穿得越多,这是反常识的地方。轻薄的布料不能隔热,只有厚重的夹棉衣才能保护人体。
“沈工!”
不远处,一个文书模样的人跑来,气喘吁吁,举起一叠文件。
在工人之间,有个人走出来,解开棉服。他戴了副金丝框眼镜,看起来四十多岁,皮肤因为暑热而泛红,沾染灰烬。
“沈工,英国的检验报告还是磷含量过高,强度不合格,您看。”文书说着,举起文件。
沈兆霖翻看片刻,从上衣口袋取出钢笔,在末尾的处理报告上签字。
“按照废钢回炉。”他说。
“师父!”何永年叫道。
沈兆霖抬起头,逆着阳光,渐渐地笑起来。
那天黄昏,他们在沈兆霖家中第一次聚餐。保姆料理鲈鱼,并为大家温了一罐黄酒。
“师父,有件事我不明白,”陈文修说,“明明都属于汉冶萍公司,大冶的铁矿为什么要先卖给日本人,剩下含磷量高的次等矿才给我们?”
“不是这样讲。日本八幡制铁所与我们签订采购合同,按日本的矿石标准验收,合格的才会收购。他们的采购量毕竟有限,剩下的也有优质矿石,”沈兆霖思索片刻,低头夹了块鲈鱼,“当初做钢轨时,就已经是这个局面,我们的品质并没有被制约。”
“可我听说,钢轨试件常常在英国检验含磷过高不合格,沪宁铁路就是因为这个才不用国产钢轨。”
“沪宁铁路总工程师是英国人,材料采购也由英方代理,必然会倾向进口,我怀疑检验结果从那时起就造假。若真如报告所说,川汉线用了我们的钢轨,必不会运行二十年而无事故。归根结底,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检验机构。若要打破桎梏,必当建设独立钢铁体系,不可受制于西洋。”
“我中华国土辽阔,如秋海棠叶,一定有许多未发掘之矿藏,”何永年笑道,“或许我们能找到优质铬钼矿,提升钢材性能。”
陈文修附和。沈兆霖却仰起头,眉锋微蹙,似乎想到什么。
“你们知道,我本来主修物理学。我常想,物理学研究真理,放之四海皆准。但冶金学不同,研究的是方法,应当因地制宜。中国矿藏与西洋本就不同,西洋研发电炉,精确调控温度,使钢水结晶均匀,仿佛高炉产出的铁一定要精炼成钢才行。若只研究高炉冶铁方法,舍弃精炼,是否能发展一套不同的,更廉价、且好推广的材料体系?”
第三章
第三章
师父叫了几个人,把试块送到材料检验室,分析元素成分。
民国钢铁牌号用的是CNS标准,类似日本的JIS标准,如今台湾地区仍在使用。HYLn不符合CNS牌号编码规则,显然是厂家自定的标注方式。
我把笔记本带回办公室,偶尔翻阅。第一页是张墨蓝色钢笔勾勒的速写,树木掩映的大门后,一条路笔直地通往红砖厂房,远处隐约看到高炉和烟囱的轮廓。后面半是学习记录,半是日记。那些手写的繁体字和竖排方式初读时有些困难,读过几页后就顺利许多。
笔记的主人名叫陈文修,毕业于北洋大学,民国九年入职汉阳铁厂。带他的师父叫沈兆霖,是晚清留英学生,主修物理学。同年入职的何永年和他住在一个宿舍,也频繁出现在笔记中,看来两人关系不错。
在沈兆霖提出建设新的,以铁为主的材料体系时,陈文修感到惊讶。在他接受的西洋机器学教育中,钢比铁性能更好,是冶炼的最终目标。这一点没人置疑过。如果不再炼钢,而是注重冶铁,材料体系会发展成什么样?他从没想过,我也没想过。
钢和铁的区别是什么?
在这段记叙的末尾,陈文修写下一句话,后面几页是关于元素含量的计算。
以现代材料学定义来看,钢和铁都是铁碳合金,碳含量小于2.11%是钢,大于2.11%是铁。高炉冶铁,用高炉产出的铁加入转炉、平炉或者电炉精炼得到钢。
钢的含碳量小,强度和韧性更高,可以锻造和滚轧,获得更高的力学性能,而铁一般只能铸造,并且容易生锈。总体来说钢的性能更好,成本也更高。
我把笔记逐页拍照,传到公司内网。师父偶尔会看,从内网聊天软件上发来段落截图。
“我知道沈兆霖的想法,以铁代钢,以铸代锻,这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做法。它确实符合中国国情,也推动了新中国工业发展,但随着精炼技术的提高,这个思路很快就退出了主流。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了。”他说。
“稀土球墨铸铁?我查到了,它的性能接近于钢。”我一边搜索,一边截图打字。
“添加稀土元素铈的球墨铸铁,强度高,耐磨性好,可用于受力复杂、强度和韧性要求较高的零件。”
“是的,他们应当是想研发稀土球墨铸铁。中国稀土储量大,国际上占有优势,理论上可以超越西方。但陈文修入职是民国九年,也就是1920年,那时中国还没有大规模开采稀土矿。不过也不排除他们得到少量样本的可能。”
如果是这样,试块上的钢印牌号就很好解释。HY是汉阳缩写,Ln是镧系稀土元素。就像美国Haynes International公司的哈氏合金,牌号就没有采用美国ASME材料标准,而是全用HASTELLOY开头,自成体系。
“你是说,那牌号的意思是汉阳镧系铸铁,第103号试件?但他们是怎么找到稀土矿的?”我问。
师父没回话,应当是在翻找照片。
我继续查阅稀土球墨铸铁的材料。在以铁代钢、以铸代锻的风潮过去后,稀土铸铁并没有退出市场,而是因为优异的耐腐蚀和耐磨性,被广泛运用在耐酸泵、阀门和容器中。在此基础上,更是发展出了可以用于航天的稀土钢。
过了一会,聊天软件闪动,是师父发来的一张截图。
“我翻到了,他们找到了独居石。”他说。那是一种稀土矿,但由于存在放射性元素钍,近年来很多地区已经禁止开采了。
第四章
第四章
1911年春,英国曼彻斯特大学。
沈兆霖坐在后排,翻开笔记。偌大的礼堂里座无虚席,前方的讲台上竖着一块黑板。欧内斯特·卢瑟福教授坐在一旁,他的助教在黑板上画出一些试验装置的示意图。
“将放射性元素铀放进铅盒,只留一个小孔,就会形成一束放射线。在附近放置一块磁铁,射线就会分为三束,一束不受影响,一束稍微偏转,一束偏转严重,这证明它们分别携带不同的电荷。我们把它分别称为γ、α、β射线。”
助教画出三条射线,并在它们外侧用椭圆圈住。
“如果用金箔纸记录射线落点,会看到大约每8000个α粒子,就有一个移动方向偏差超过90°。所以我们设想,原子结构与太阳系类似。大部分质量和正电荷,集中在很小的中心区域,类似太阳,而电子则在此区域外运动,像行星一样。这就是卢瑟福教授提出的原子行星模型。”
学生们开始窃窃私语,在此之前,最为流行的原子结构学说是梅子布丁模型,即认为原子是带正电的球体,负电荷镶嵌其中,就像梅子镶嵌在布丁里。
“原子核就是一颗恒星,电子是行星,而维系它们平衡的是强磁力和强核力。这个平衡一旦被打破,将释放出不可估量的能量,像太阳一样。”助教说。
有学生提问,卢瑟福教授一一回答,最后对他的理论做出总结。
公开课后,沈兆霖走出教室,他约的人已等在那。
许杭站在草坪上,斜倚围栏,明明面容姣好,却穿了一身男式洋装,少年意气。她出身富商家庭,奉行冒险主义,反对传统婚姻,与沈兆霖算是远房表亲。在沈兆霖求学十几年中,许杭早已走遍世界,俨然成为一位旅行者和探险家。
“沈兄,”许杭招手笑道,“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,你还是对物理感兴趣。当初你要是留下,现在也能站在台上了吧。”
沈兆霖摇了摇头,走到她身旁。
“人总要向现实妥协,这也是我的选择。一个国家没有工业体系,就算用物理学推导出模型,又怎样去试验,去制造应用?所以我转修冶炼学,并不后悔。”
“和林小姐分手也不后悔?现在人家可在伦敦定居了。”
“别提这事。我是出差,明天就走。下次回国,你得去找我。”
“好吧,先去吃饭。”许杭耸了耸肩,手伸进口袋,忽然挑起一侧的眉毛。
“这个先给你,免得忘记。你猜我是从哪得到的。”她说着,从口袋里拿出一只玻璃标本瓶。
里面是一些矿石标本,棕红色晶体,表面油脂温润,带有玻璃质感。
“独居石?”
沈兆霖举起瓶子,对着阳光查看。那些红色的折射光很美,像流动的铁水。
“对,你现在做钢铁冶炼,我想应当有用。你看品相怎样?”
“杂质很少,挪威还是瑞典?”
“不,是蒙古草原,白云鄂博。”许杭又一挑眉,对沈兆霖的惊讶早有预料。
“起初我也很意外,”她说,“本来我是去猎狼的,生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。老乡说那里还有很多,我雇人收集了。等你回国,我让人给你送到汉阳去。”
沈兆霖对此感到兴奋。国际上始终认为稀土储量少,适合研发高精尖钢种,甚至因为成本高而放弃这个方向。中国如果有大量未开采的稀土资源,便可由此超越西洋,建立不同的钢铁体系。
回国后,他用试验法从独居石样本中提取少量稀土元素,随即向铁厂提交了稀土铸铁提案。然而,当时政局动荡,不久之后一战爆发。铁厂侧重产出军用钢材,没有批准提案。直到陈文修入职的时候,一战已经结束,稀土项目才开始立项。
陈文修和何永年顺理成章地进入项目,学习用碱水池提取元素。他们从独居石中分离出了多种稀土元素,但由于国内没有检验设备,无法确定具体元素,于是统一用镧系代表,称为汉阳镧系铸铁。
许杭提供的矿石虽然不能成批量,却足够支撑试件制造。
三年时光一晃而过,他们制造出若干添加不同镧系元素的铸铁试件,准备一同送往英国检测,然而沈兆霖却渐渐消瘦,脸色苍白,偶尔咳嗽。
那天下午,陈文修照例从竖梯爬上炉口,观察铁水颜色。因为身体缘故,沈兆霖最近很少到现场来,这里除了几个工人,就是他和何永年轮班值守。
高炉旁不远,是早上灌入铸模的铁锭。他填完记录,看了眼手表,写下时间。还不到五点,可天已经有些暗了。应当是因为过了秋分,白天正在变短,可这短得也有些快。陈文修想着,却看到那几个工人脱掉防火服,收拾起饭盒和随身的东西,往门口走去。
工人有时候偷懒,提早溜出去,但不会这么明目张胆,当着他面来。
“你们上哪去?”陈文修有些不悦,叫住几人。
“下班了,陈工。你不走吗?”
“还有一个多小时。”陈文修又看了眼手表,确认时间。他开始隐隐察觉哪里不对,却捕捉不到。
“明明六点整了,你不能不讲理啊。”
工人面露诧异,指向院门外。
陈文修抬起头。门口的办公室里有台座钟,面对玻璃窗。现在,它的指针刚过六点。因为要严格控制冶炼时间,他每天晚上都会调手表,怎么会出错?时间记错,意味着他今天的冶炼记录全部作废,这是从没发生过的事。
陈文修感到后背发冷,跑到窗口,低头反复检查手表。他很快看出了问题,手表的秒针并不是匀速转动的,而是停滞一会,再跳上几格。
窗台上有几块铸铁废料。在他无意间移动手腕的时候,秒针靠近铸铁时停滞,离开时加速跳跃。这说明表针被磁化了。这是长时间处于强磁场内的结果,而他今天一直在高炉旁。融化的铁水不可能有磁性,那么磁场来源就是那块正在冷却的铸铁。
工人们已经走了,院中空无一人。在他思考的时候,身后忽然传来几声异响。陈文修转过身,正好看到一颗螺钉在地面旋转飞起,叮的一声撞到铸件上。
附近的铁器开始发出细微的颤动。随着温度的降低,铁原子和稀土原子正在结晶,形成一种全新的,未知的强磁结构。
第五章
第五章
材料室的晶相分析报告很快通过内网上传,试验员通知了我。我点开翻看,这是一份典型的稀土球墨铸铁分析报告,稀土元素铈的含量和球墨晶相结构与现代无异。
刚过九点,大厅里格外安静。师父去饮水机接了水,端着杯子走过来,站在我身后,看着屏幕上的报告,也惊讶地发出赞叹。
“我猜这是他们在1923年做出的最后几批试块,也就是民国十二年。因为积累了经验,所以品质最高。”师父说。
“为什么是1923,你怎么知道?”
“因为汉阳铁厂1924年就停产了,此后汉冶萍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日本出口铁矿石。”
“卖给日本人?,”我愣了一些,有些无法理解,“那不是被用来造侵华战争的武器了吗?”
师父摇了摇头,没有回答,而是让我把滚动条拉上去,仔细看起元素含量的页面。
“我看过了,和现代的球墨铸铁不相上下。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直接采矿,商业化产出。稀土铸铁售价低,性能好,一定会占领市场。”
“不是那么简单,你知道民国时候的鸡立球事件吗?”师父说。
什么鸡立球,鸭立球。我以为他开玩笑,师父却低下头,从手机上搜出一张照片,放到我面前。
照片上,是英国鹰球牌特种钢宣传册,商标图是一只鹰站在地球上。
“这是英国特种钢品牌,鹰立球。1943年,中国中兴钢厂制造一批工具钢,物美价廉,但是大家不敢用,政府出面都卖不出去。直到有人伪造英国鸡立球商标,说是鹰立球的副品牌。这批钢伪装成进口鸡立球牌,高价出售,反而被一抢而空了,”他说,“当时政府公信力不足,市场一味崇洋媚外,国产品牌只能在保守领域产出,如果想推行一种新型铸铁,是没有市场的。”
这些是我从没考虑过的。我习惯从现代局势出发,忽略了当年社会结构的不同。或许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的事,在陈文修所处的时代,也是天方夜谭。
“对了,试验室那边跟我说,军工项目组要用这个试块,按他们的想法增加检测,我们不用去取了。”师父拍了拍我的椅子,从工位后走了过去。
军工组是公司内的一个部门,负责的都是有密级的项目,不好多问。
我关掉报告,处理一会日常工作,又打开笔记照片。这些记录紧凑,跳过一段就难读懂,只能按顺序看。师父最近忙,应当没我进度快。
由稀土元素制造、磁性极强的铸铁,只有一种可能:钕磁铁。如果这是真的,钕磁铁的发明时间将被提前60年。可我清楚地记得,铁箱中的试块并没有磁性。
如果铁箱是陈文修本人留下的,他一定是想用这本笔记和试块互相验证,向我们展现当年发生的事实。可如果他们最大的成果是钕磁铁,他为什么选择放入另一个试块,而不是把钕磁铁放进去,哪怕只是一小块,那不是更有说服力吗?
陈文修在笔记中写下了他的恐惧。那个傍晚,他久久地凝视着那块铸铁,就像凝视深渊,他不知道继续探究,会遇见什么。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沈兆霖。沈兆霖亲自检验过后,非常兴奋,当即决定更改船票,提前去英国的日期。
“永年跟我一起去,”他说着,回头拍了拍陈文修,“你在家,看好设备。”
“真的?”何永年跳起来,忽略了陈文修眼中一闪而过的失落。
一起工作的三年里,何永年显然更得赏识。陈文修感到沮丧和孤独,这是之前少有的情绪流露。
何永年的父亲在国民军任职。他和沈兆霖是一类人,优渥的家庭条件让他们从小视野开阔,头脑灵活。陈文修感到了自己和他们的差距,那不是努力就可以弥补的。
沈兆霖和何永年在一个清晨出发,工人调去了别处,偌大的高炉旁只剩下陈文修一人。他当时不知道,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聚了。
第六章
第六章
民国十二年,冬。
凌晨的上海渡口,从英国来的渡轮刚刚靠岸,旅客鱼贯而出。
天色晦暗,太阳还没升起,街上行人寥寥。在旅客末尾,何永年提着皮箱,跟在沈兆霖身旁。他们身上有长途旅行的疲惫和落寞,尤其沈兆霖,脸色比出发前更加苍白。
“你记得吗?原子核就是一颗恒星。磁力和核力……”沈兆霖说。胸中的闷痛让他感到时间紧迫,急于说出构思。
“师父,回去再说,我去前面看看。”何永年紧了紧围巾,环顾四周,没发现黄包车。于是他放下皮箱,走进前方的小巷。
沈兆霖独自站在那,周围安静,几只麻雀落在纵横的电车线上,又扑棱棱地飞走。他忍不住咳嗽一阵,拿开手帕时,上面已沾了斑点血迹。沈兆霖折起手帕,塞进口袋,冥冥中感到黑影闪动,回过头望向灰蒙蒙的渡口。
在那一瞬,黑暗中火光闪过。一颗子弹擦着他的鬓角飞过,不等他反应,第二声枪已经响起,子弹从侧面穿过了他的胸腔。
何永年带着黄包车跑回来的时候,沈兆霖的身体已经冰冷。
警局的解释是遇到劫匪,可他们的财物并没有损失,包括那只染血的皮箱。
陈文修得知消息是在几天后。从警局回来的何永年好像变成了一个空壳,反应迟缓。
陈文修跑过去,扳过他肩膀。皮箱上的血已经干涸,试块与出发时一样,多的是一沓英文检验报告。陈文修打开看,所有报告只有强度部分,没有化学分析,包括那块强磁铁。参照结构钢标准检测,试块强度全部不合格。
“怎么回事,师父最在意这块磁铁,怎么会不检测磁性。还有化学成分,不是说要确定稀土元素吗,为什么没有成分分析?”陈文修站起来,见何永年还是没有反应,一把抓住了他的领子。
“如果只是检验不合格,怎么会有人刺杀,你为什么不说话?!”
何永年咬紧牙齿,一言不发,这让陈文修怒气上冲,一拳砸在他脸上。
“陈工!”工人扑上来,拉开陈文修。
何永年没还手,只是啐掉了嘴角的血。
“你想知道为什么,”他说,“因为原子的中心是一颗星星!”
何永年撞开陈文修,用袖子抹干净脸,冲出大门。
当天晚上,何永年没有回来。他向公司申请调换宿舍,并要求休假。
沈兆霖的葬礼在圣诞节前。他的父母已经过世,家里只来了一位堂兄。
在一众朋友和同窗中,陈文修见到了许杭。她也已经四十多岁了,依然西装打扮,只是烫了卷发,淡妆下的脸庞有些岁月痕迹。
许杭走过去,摘下贝雷帽,将一束白兰花放在墓碑前。过了一会,她把手伸进口袋,摸出一枚戒指,放在白兰花上。
“这是林小姐托我带给你的。”许杭顿了顿,然后像是想到什么,微微一笑。
“林小姐,现在是特里夫人了。”
许杭站起身,向等候的工人们示意。在沈兆霖的墓旁,早已挖好另一个深坑。工人将许杭带来的木箱连同一些遗物放进去,填上泥土。
这是她带来的最后一箱独居石。随着沈兆霖的死亡,稀土铸铁项目被取消,这些也就都没用了。之后不久,因连续亏损,汉阳铁厂停止炼钢。何永年被调入汉冶萍公司贸易部,负责向日本八幡制铁所出口铁矿石。
停产后,工人被遣散。陈文修不愿离开,申请作为设备维护员看守车间。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心结,他要弄明白沈兆霖是为什么而死。通过试验车间里的蛛丝马迹,明白那些对他遮掩的,咫尺天涯的真相。
原子的中心是一颗恒星,电子是行星,维系它们平衡的是强磁力和强核力。陈文修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,这是何永年最后的答案。强磁力,磁铁……
笔记在这暂停了下来。后面还有内容,只是墨色不同,字体也变得潦草,显然是几年后续写的了。
第七章
第七章
笔记中的时间有十年空白,陈文修再落笔的时候,已是民国二十四年。
政府组织钢铁行业标准编制,他向汉冶萍公司提交了一套稀土铸铁标准方案,很快被退回,没有采用。
彼时,何永年已升任大冶矿贸易部副主任,娶妻生子。在方案退回后不久,他忽然找到陈文修,请他吃饭叙旧。
这是他们斗殴后第一次相见。何永年的样子已经变了,远离体力劳动的工作让他皮肤白皙,腹部脂肪堆积,谈吐作风也大不相同。
他从酒楼叫了几个菜,送进宿舍,并提出要打通关系,把陈文修调到大冶矿,那里工资更高。陈文修没有回应,他知道何永年为什么突然出现。
“你想问我什么事?”陈文修夹起鱼肉塞进嘴里,又灌了口酒。酒味和沈兆里家里的不同,稍有些涩。
“不,我们这些年没见,只是叙旧,”何永年笑道,“文修兄可一点没变,不像我俗事缠身,已经老了。”
“你想问我高炉停了十年,没有独居石,也没有试验条件,我是怎么编出那本标准的?”
“我只是想,当年我们那么好,每天在一起。可是师父一走,就好像什么都没了。”何永年说。
陈文修低着头,仿佛在做某个决定。过了一会,他忽然起身,抓住何永年的胳膊,向外走去。
“你跟我来。”他说。
屋外夜色漆黑,树木的影子在路旁晃动。穿过小路,拐几个弯,就到了一座偏僻的厂房前。
陈文修移开堵在门口的木板,点燃煤气灯。
这里很久没有外人来过了,两侧的空间被照亮,何永年看到堆砌的试块,再往前走,灯光就落在一片巨大的黑色油布上。
陈文修放下灯,在黑暗中扯下那块布,巨大布料坠地声回荡在厂房中。幕布后是一件巨物,在灯光中影影绰绰。
“还记得你当年说的话吗?”他说。
“哪一句?”何永年怔一下,面对那巨物,有种奇异的预感。
“原子的中心是一颗星星。”
陈文修转身,走到错综的电路旁,拉开电闸。
在那一瞬,厂房顶棚的灯亮了起来,同时,巨物中传出发动机的震动。那是件两层楼高的环形设备,外侧被磁铁包裹。在它内部,一些流体随着通电涌动起来,发出耀眼光芒。
何永年身上的钥匙颤动起来,发出嗡鸣。他意识到面前的设备就是沈兆霖当年画在图纸上的东西,外层的磁铁就是强大的稀土磁铁。
“你哪里来的稀土矿石?”何永年伸出手,却退后几步,仿佛是看到了鬼,腿一软坐到地上。
“你挖了师父的墓。独居石,还有图纸……你挖了他的墓!”
陈文修走过去,向他伸出手,但何永年察觉了他眼中的疯狂,向后退去。
“你们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见过卢瑟福教授,欧内斯特·卢瑟福,”陈文修说,“师父本来就是他的学生,他根据卢瑟福教授的理论设计出一件设备,这些图和文件就压在独居石下,我用了五年时间看懂它。”
“仿星器……”何永年自语着,转头望向那巨大的,正在发出嗡鸣的,闪烁流光的机器。那是仿星器,根据欧内斯特·卢瑟福行星理论和原子结构设想出的,永磁铁和线圈构成的核聚变装置。那些闪光的磁流体在电磁场中模拟恒星内部的聚变,或者可以说,他制造出了一颗星星。
“这些东西就应该被埋葬!你不懂!”
何永年忽然爬起来,顾不得拍身上的土,一把抓住陈文修。
“我怎么不懂?师父虽然没特意教过我这些,但他教你的时候,我就在旁边,我找到图纸,把它做出来了,我怎么不懂?!”
“他太理想化了,沈兆霖太理想化了!”
他突然喊出师父的名字,陈文修愣了愣,耳中蜂鸣。
“匹夫无罪,怀璧其罪。你不懂吗?!仿星器的下一步就是武器,释放原子核能的武器,比一万吨TNT威力还要大!你们说我出口铁矿石给日本,是卖国,是要制造武器来杀死中国人,但如果当年师父回来,产出永磁铁供给英国,又要死多少中国人?!”
陈文修从没有这样想过。他和沈兆霖一样,刻意忽略了仿星器的杀伤力。然而何永年不同,他天生敏锐,本该从政。此刻,面对着何永年的眼睛,沈兆霖遇刺的真相隔着一层纸,陈文修却不敢问了。
第八章
第八章
“你看到了吗?”师父不知何时走到我身后,拍了拍椅背。我毫无防备,急忙保存了正在编制的工艺卡,转过头去。
“什么?”
“那本笔记,他组装出了仿星器,用永磁铁!”
师父神情激动,手里的手机屏幕还亮着,显然刚刚打完电话。
我昨天读到陈文修续写的记录。铁厂停产的十年中,他用永磁铁和电线组装出了沈兆霖设计的仿星器。我从没听过这个名词,也没有细想那是什么。毕竟一百年前的东西,再怎么说也是落后的了。
“可控核聚变你知道吧?”他见我懵懂,指了指书架上的行业杂志。
“中国的托卡马克试验器,人称人造太阳,前几天投入运行,刚上过新闻。”
“我知道托卡马克,那就是仿星器?”
“不,可控核聚变在最初主要有两种设计方案,一种是托卡马克,一种是仿星器。而现在,我们几乎听不到关于仿星器的研发,是因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仿星器的设计由于粒子损失大被大部分国家放弃。现在国际盛行的就是托卡马克。但它有一个明显的,难以攻克的问题。你可能听过,可控核聚变的实现期限永远是还有五十年,从某种程度上说,它的研究卡住了。”
“什么问题?”由于专业限制,我确实没想过这一层,被勾起好奇。
“连续和稳定的磁场,”师父说,“托卡马克的磁场不稳定,而仿星器内部是流动的电浆,外部线圈和磁铁能连续稳定地维持磁约束。近年来,日本和德国已经转向仿星器研发。粒子损耗可以克服,或许与托卡马克相比,仿星器才是更现实的核聚变方式。还记得我说的军工项目组吗?他们就加入了仿星器的可行性研究,任务是研发强磁性稀土磁铁,所以才会拿走试块,没想到这下正中靶心了。他们的仿星器能够运行,一定有独特的设计。”
“可我们怎么证明他写的是真的,不是虚构?如果是真的,他为什么不把钕磁铁试块放进铁箱,而是放了块无磁性的稀土铸铁试块?”
我问出一直想问的问题。师父摇了摇头,从书架上拿出笔记,翻到最后几页,展到我面前。那天晚上,何永年留宿在铁厂宿舍,说好次日带走稀土铸铁方案和仿星器设计图。陈文修在凌晨醒来,内心的不安促使他打开何永年的提包,在里面发现了手枪和一封日文信。
何永年本来就负责与日本八幡制铁所对接,这很正常。但陈文修发现那是一封私人信件,他不懂日文,却认得出其中夹杂的英文单词和汉字:Magnetic,技术……无国界。
最后的笔迹很慌乱,显然是在赶时间。何永年的弹匣里有四枚子弹,他全部卸下来,藏进贴身口袋,将空弹匣装了回去。
“如果这就是结局,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。”笔记的最后这样写道。后面的纸页全被撕掉,留下参差的断茬。
“这天是民国二十四年,五月十九日。军工组的人刚刚告诉我,他们查到了汉阳警署的出警记录。那天清晨,有人在铁厂附近的汉江边听到两声枪响,警察赶到后,只在杂草中发现打斗痕迹,其他一无所获。几周后,铁厂负责人报警陈文修和何永年失踪。这桩案子一直没有结,后面没有再记录。”
“他们查这个干什么……”我愣了愣,忽然脑中灵光闪过。
“他们要找那台仿星器……不,是仿星器的设计图!”
“对,仿星器的研发有技术断代,沈兆霖的设计方案很重要。三年后,也就是1938年日军入侵,国民政府成立钢迁会,将汉阳铁厂迁往重庆。无法运走的设备被主动炸毁。当年时间紧迫,又有日军轰炸,没有条件辨认检测材质,仿星器很可能被一起炸掉,投入汉江了。但我觉得,陈文修保留这本笔记和试块,一定是有意义的,他想表达什么?”
是的,他想表达什么?如果他害怕日本人发现铁箱,不肯放入磁铁试块和仿星器资料,那么
被放入的这些东西又指向哪?
我和师父没有讨论出结果。加班结束,走下公交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。市中心的灯光璀璨,隐没星光,而我租住的房子靠近市郊,在这里抬起头,就依稀能看到群星的影子了。
“原子的中心是一颗星星。”这句话从脑海中闪过。从汉阳到曼彻斯特,在高炉融化的铁水旁,在漆黑寒冷的太平洋轮船上,沈兆霖大概无数次凝望夜空,试图用永磁铁和线圈仿造、复制那颗恒星。
在路灯似有若无的光芒里,我仿佛看到陈文修,穿着米白的洋布衬衫,走出破败停工的铁厂宿舍。
“回到故事的开头。”他说。
故事的开头是什么?是陈文修走出汉口火车站,是沈兆霖在英国转修材料学,还是许杭送来独居石,他们三个炼出第一炉稀土铸铁?
那些画面倒放闪过,直到停在驶过汉江的黄包车上。那时何永年刚刚毕业,目光清澈,微笑着转过头。
“文修兄,你会水吗?”他说。
我感到心脏猛地跳动,抓起手机,按下号码时手有些抖。
“喂?”师父接起电话,我已喊了出来。
“在江底,江底的藏金洞!笔记是线索,陈文修把仿星器的设计图放在了江底!”
第九章
第九章
重庆钢厂搬迁前,我已经辞职回到北方,进入天津铁厂。
那座钢迁会的库房并没有被拆除,而是保留下来,成为重庆工业博物馆的一部分。事实上,现在整个重庆钢厂的冶金车间都属于博物馆了。
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发展,再到冷清,前后时间不过一百年。
我师父已经退休,偶尔还和我联系,聊些家常。
那晚我给他打完电话,他通知了军工组。不久后,一支设备齐全的潜水队潜入汉江,在江底深处果然发现一处半米宽的石洞。
他们翻开洞口的石头,找到一包蜡封并用油布裹紧的资料。师父说那里除了仿星器设计图,还有一份钕磁铁的冶炼记录,详细到元素配比和保温时间,具体数据就不是我能接触到的了。
去年秋天,我因为业务关系到武钢出差,第一次到达汉阳。下飞机时,迎面是熟悉又久违的南方潮热。
铁厂旧址已经建起艺术展馆。龟山北麓的纪念园里,有块200吨重的巨大凝铁,是当年停产前,高炉坍塌造成的遗迹。
我特意来到汉江边,迎着风站了一会。
现在已经没人在这游泳了。江水浑浊,缓缓而下。而这水面下,就是陈文修当年想到的,最安全的地方。
那两声枪响被记录在汉阳警署的案宗里,真相是怎样?
人是会变的。二十七岁的何永年不会想到,他会变成自己憎恨的样子。
面对日本人的觊觎,陈文修不需要转移几吨重的永磁铁,他只需要解决何永年。没有何永年这条内线,他们就算能顺利进入铁厂,也找不到仿星器。
从一个人手里夺走枪,比夺走子弹容易。陈文修或许在江水中向何永年开了两枪,带着资料潜入江底,可如果一个人不戴设备潜下去,还能回来吗?
时间倒转几小时,是日出前的凌晨。
陈文修写完最后一笔,找到他们三个做出的最后一件试块:HYLn-103,把它和笔记锁进铁箱,然后将图纸和记录密封,揣进怀里,返回宿舍。
“永年兄。”他拍了拍何永年的肩膀。
何永年虽然睡着,警惕性却极高,下意识翻了个身,摸到床边的提包,那把枪还在里面,轮廓清晰。
“资料整理好了,明天给你。我们再去江里游一次泳?”陈文修说。
在那一刻,或许是因为似醒非醒,何永年忽然感到恍惚,就像回到十年前,无数个盛夏的清晨。他们会在开工前出去游泳,有时趁着天黑,回来正赶上铁厂的早餐。
铁厂旧址就在不远处,我沿着江走过去,戴上耳机,点开新闻。
“近日,我国在仿星器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由于采用创新性结构和稀土材料,仿星器试验体预计将实现稳态运行。该项目完善了中国磁约束聚变体系,改变了以托卡马克为主的以往研究方向,为受控磁约束聚变能源开辟了另一条技术路线。为纪念对创新结构作出突出贡献的工程师,试验体仿星器被命名为汉阳一号……”
播报声渐渐隐去,画面上,那环形的巨物被线圈和磁铁缠绕,内部的蓝色流体在启动瞬间发出耀眼光芒。
我关掉屏幕,江水随着视线延伸,隐没在远方,就像没有尽头。
审校:宇镭、于苏斯